以下文字选自《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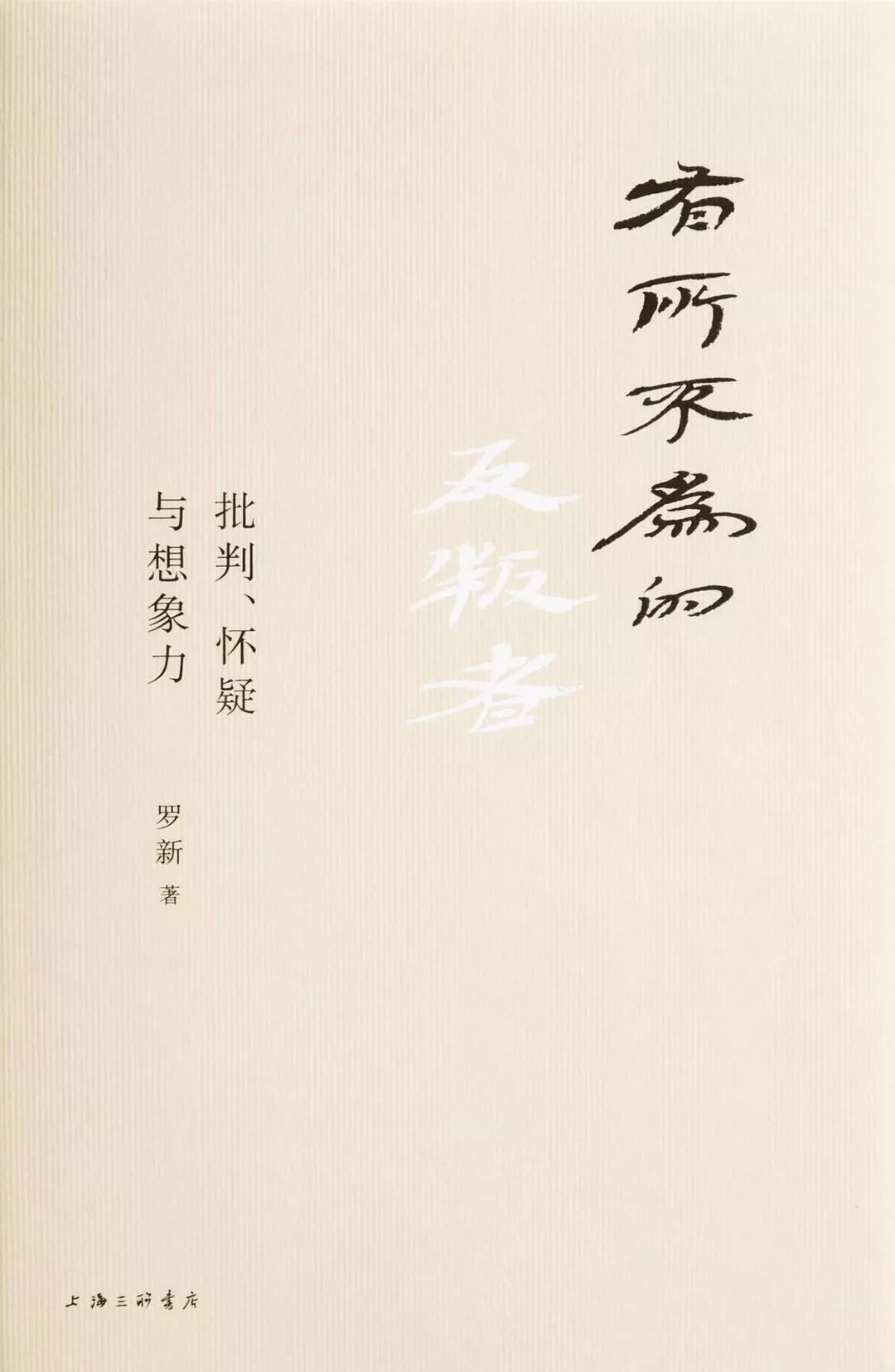
作者: 罗新
出版方: 理想国 |上海三联书店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帝国是从匈奴开始的。从匈奴到蒙古,一千五百年间,无论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欧亚定居社会如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诸国、东欧和中欧诸国曾经如何强盛,当他们面临草原游牧军队的铁骑时,都显得那么笨拙和孱弱。自古以来,以定居文明为本位立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都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为什么拥有高度文明和伟大传统的农业国家,竟如此经不起那些乍兴乍灭的草原政权的猝然一击?除了大肆渲染并极力夸张游牧军队的残忍和野蛮,难道就只能把定居文明的失败归因于定居文明自身的政治腐朽和王朝堕落吗?传统的历史学家无法解释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困境。
这就是我们关心匈奴的原因。现今有关匈奴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许多疑问、猜测和误解,有不少神话成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匈奴的西迁。东汉中期漠北的北匈奴被鲜卑击破之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似乎就再也没有以高级政治体的形式在中国史籍中出现,汉文史籍明确以匈奴余部相称的游牧集团只在西域有零星出现。《后汉书》说“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已经指出在北匈奴的政权破灭后,原匈奴帝国统治下的人群被新的统治集团—鲜卑人所吸收的事实。但是,当18世纪中期的法国东方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从传教士那里获知中国历史上有个匈奴(Hsiung-nu)时,就立即联想到西方历史上的匈人(Hun),二者名称上的近似使他相信匈人就是西迁后的匈奴,并写进《匈奴、蒙古与其他西部鞑靼的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 des Mongoles, des Turc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1757)。德经这个联想经著名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援引入读者面极宽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很快成为一种流行说法。

后汉书
然而,从北匈奴破灭到匈人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边陲诸省,其间年代学上的断裂长达二百多年。为弥补这种断裂,研究匈人的一些西方学者把许多不相干的历史事实联系到一起,为匈奴西迁编织了年代上和空间上的连续历史。当然,这些编织大都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依据的,早就被现代严肃的内亚历史文化研究者所否定。把匈奴与匈人联系起来的尝试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在当今的中央欧亚研究者中几乎已成共识。除非出现进一步的证据,匈人乃西迁的匈奴残部这个说法已很难再回到学术讨论里。有趣的是,在中国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说法信为确论,津津乐道。这个现象本身,足以说明匈奴历史中存在着许多非历史的内容。
但要正确解读匈奴的历史也非一件易事,因为匈奴人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匈奴不像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那样各有自己的文字与文献,记录匈奴历史的文献资料全都是由对匈奴持敌对态度的汉朝官员用汉文写下来的。汉文史料提供了描摹匈奴历史轮廓几乎唯一的依据,而教科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都来自这些依据。汉文史料以可靠性高而著称,但关于匈奴人和匈奴国家的起源、发展、衰落与去向,仍然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空白。匈奴不像突厥那样与东亚文明圈以外的波斯文明和罗马(拜占庭)文明发生深刻碰撞,也没有像突厥那样,由突厥人自己、也由周边的定居文明国家(如唐朝和波斯)留下了许多反映突厥人相貌的雕塑和绘画。
就欧亚大陆的历史来说,匈奴帝国是在以连绵草原为主要地理特征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出现的第一个骑马游牧人建立的大型帝国,幅员之辽阔,足以与同时代任何一个定居王朝相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匈奴人是何时成为游牧民的,更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以及向谁学到了建立庞大国家组织所需要的政治技术。现在学术界相信,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游牧,要比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出现晚得多。游牧的基本要素是马的驯化和骑乘,这种技术到底是从南俄草原上兴起从而逐渐传播到东部的蒙古草原上的,还是多元起源、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到现在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草原政治体高级形态的匈奴帝国的出现,绝不应当是像它在史料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突如其来。

匈奴帝国
在匈奴帝国崛起以前,中西史料都记录了欧亚草原上某些游牧集团或准游牧的人群力量,比如希罗多德所记录的斯基泰人,以及中国先秦史籍中的各部戎、狄,但把他们看成匈奴帝国的前奏,还需要有更直接和可靠的证据。对此传统文献显得无能为力,后起的考古学相对有了用武之地。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在华北、西北、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等地区的工作,为解读匈奴文化的源流,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证据和线索。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俄苏、欧美、日本、中国和蒙古等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家,在中央欧亚的广大范围内,特别是在东起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西至里海和高加索的内亚地区,发现了大量与匈奴文化可能相关的一些古老文化,如那些极有特色的饰牌、短剑和匕首等青铜器。现在已经被弃用的术语“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出现,本来是专指这类明显不同于中原传统的青铜器的。这个称谓之得名,就是因最初主要在草原南缘的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这类青铜器。但后来在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以及蒙古高原和中亚,甚至在南俄草原及里海沿岸,都大量发现类似风格的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一称遂被“草原青铜器”所取代。这类以动物图案为主要特征的青铜器的广泛分布,显示了在一个极为辽阔的空间内存在着某种连续的和共有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而这种青铜文化持续的时间早于匈奴帝国,可以设想,后来建立了匈奴帝国的早期匈奴人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匈奴帝国是某种历史悠久又分布广泛的古老文化的产物。
语言学研究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匈奴的历史渊源。比较语言学家把匈奴之后蒙古高原上曾建立过高级政治体的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集团,都看成阿尔泰语系人群。无论是从比较语言学还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看,阿尔泰语系诸人群之间都存在着较强的关联。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各自建立的王朝以及这些王朝所支配的草原社会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与一致性。那么,这种连续和一致是在匈奴之后才出现的吗?匈奴的历史,匈奴所属的那种古老文化,与鲜卑之后的阿尔泰文化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逻辑上这个问题也许不难回答,可是要获得学术论证,则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2004年,在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协助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组织的“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队”来到蒙古国的图拉河(Tuul Gol)和鄂尔浑河(Orkhon Gol)流域,考察的重点是该地区匈奴至契丹时期重要的历史遗迹,包括城市聚落遗址、墓葬、岩画和纪念碑。其中属于匈奴时期或比匈奴还要早的遗迹,主要是墓葬和古城址。

图拉河(Tuul Gol)
匈奴墓葬考古最著名的是俄罗斯人在蒙古国诺颜乌拉发掘的大型匈奴贵族墓地。我们在图拉河北岸也见到一片方圆约十公里的巨型墓葬区,时代早于匈奴,属草原青铜时代。这个古墓葬区被巨大的方形石墙整齐地分隔开,每一个圆形石堆墓葬都被多层次的方形石圈所分隔,而整个墓葬区又被复杂而宏大的方形石圈里里外外地分隔。这和我们常见的北疆古代石堆墓和石圈墓既有近似也有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规模更大。
在图拉河南岸达欣其楞县境内靠近哈尔布赫(Har Buh)河谷的缓坡草原上,也有一个匈奴墓葬群。俄罗斯考古学家在墓葬群中发掘出一些陶器和青铜器,显示出与蒙古其他地区所见的匈奴墓葬具有共同特征。
2005年夏,原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先生参加美国与蒙古的合作项目,在塔米尔河(Tamir Gol)北岸草原上主持对一组匈奴墓地进行发掘。他们除了找到许多明显属于草原游牧社会的物品,如铜饰件、皮制品、陶器以外,还发现了许多有鲜明东汉特色的物品,如漆器、铜镜、五铢钱等。这为墓葬断代提供了确切的依据。有意思的是,东汉时代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集团以后,仍然控制着漠北草原的北匈奴几乎完全失去了与东汉政权友好往来的机会,双方不再有正式的通使和贸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要得到东汉的大宗物资应该很不容易。塔米尔河谷匈奴墓葬的发掘,提示我们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匈奴也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与中原的商贸联系。历时数百年的漠北与中原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并没有轻易地断绝。
我们在鄂尔浑河流域考察时,也曾进入鄂尔浑河的支流塔米尔河河谷,专程前往匈奴时代的所谓三连城。塔米尔河水量很大,河谷青草茂密,桦树成林。溯河西行,一路上所见,都是河谷草原的美丽景象。三连城位于塔米尔河北岸的Hudgiyn Denj,三座大型古城东西并列分布,故称三连城。从土墙侵蚀的情况看,时代相当早。三座城都接近方形,由于尚未进行科学发掘,古城的确切年代现在还不能确知,蒙古学者推断为匈奴时期。但是具体是匈奴的什么时期呢?是匈奴全盛的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还是北匈奴时期?这涉及我们对匈奴社会中定居因素和农业因素的分析。

三连城
塔米尔河河谷大量的匈奴文化遗存,显示这个地区在长时期内是匈奴的核心统治区,很可能是单于庭所在。2006年7月,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新疆吐鲁番文物局等单位学者组成的“中蒙联合考察队”再次来到塔米尔河河谷,在巴特曾格勒县考察了两处大型匈奴墓葬群,一处是索勒毕山(Solbi Uul)山前墓葬群,一处是呼德根陶勒盖(Hudagiin Tolgoi,意为“有水井的山头”)大型匈奴墓地。前者位于塔米尔河西北岸,正对着宽阔而美丽的塔米尔河河谷。这片缓坡上分布着多个墓群,都是呈南北向链状排列,墓葬总数有四十余座。圆形石圈所环绕的中间凹陷部分,应是长方形竖穴,这与中国境内所见的匈奴墓非常接近。形成凹陷的原因,是原来墓穴顶部覆盖有木头,覆以堆积封土,木头朽烂后封土下沉,遂形成凹陷。呼德根陶勒盖的匈奴墓地规模更大,墓地中杂有更早时期的大型石堆墓。匈奴墓往往两两形成一组,非常有趣。
2006年夏天,“中蒙联合考察队”还在西蒙古的科布多省阿尔泰山区考察了另一种类型的大型匈奴墓葬群。位于满汗县以南十五公里处的Tahilt(意为“祭祀”)的山前戈壁上,有上百座匈奴墓葬。这处墓葬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中相当多的墓葬环有方形石圈,向南开有长短不等的石砌门道,最长的门道有十五米。这种形制的匈奴墓葬在中国尚未发现,在蒙古国亦相当罕见。这提示我们匈奴时期的文化遗迹可能反映了匈奴帝国内语言、文化、人群及社会构成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我们把匈奴时期考古发现与匈奴历史进行比对时必须充分考虑的。
研究游牧社会与定居文明冲突史的学者,大都相信这样一个前提性论断,即游牧经济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它要依赖与其他经济形式如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换,才能弥补其非自足的特性。现代人类学研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据此,一些学者相信,欧亚大陆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草原游牧人入侵农业定居社会的事例,要从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中寻求解释。骑马游牧民必须与定居农业社会交换产品,以获得草原上无法生产的农业物资。当这种交换不能以和平贸易的方式进行时,通常会演变成暴力劫掠。拥有冷兵器时代最重要战略物资—马,加上无与伦比的骑乘技术,游牧人群在与定居社会的军事较量中,总是占有一定的军事优势,主要表现在机动性和冲击力上,这种优势使得人口数量居于劣势的游牧人群在战场上却常常能集中兵力,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在这种解释框架内,游牧人侵扰定居社会的目的并不是军事占领,而是劫夺物资并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据此,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还创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上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盛衰起伏彼此对应关系的周期表。根据他这个周期表,每当中原农耕地带出现统一和强盛的王朝时,内亚草原上也会随即诞生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因为游牧人只有统一在同一个强大政权体系内,才能够有效地与南方同样强大而统一的中原王朝进行对抗,从而保证获得游牧经济所必需的农业物资。这个周期表虽然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一切农牧关系,但是影响却非常大。
不过,从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上升到游牧帝国的经济功能,这中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那就是必须证明在草原上除了游牧经济以外,并不存在或不能存在其他经济形式。而草原考古提供的大量信息对此都是否定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在非常古老的时代,草原上也有专业的金属加工业、制陶业等依赖一定程度定居生活的行业。这就是说,尽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在草原上占据统治地位,但也存在着其他经济形势,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往往是以定居为基础的,留存至今的许多城市和聚落遗址证实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的存在。塔米尔河河谷的匈奴三连城便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中国考古学家在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的调查、发掘工作中,也早就发现在游牧经济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定的农业因素。在这些考古证据的支持下,美国历史学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明确反对巴菲尔德那个著名的周期表,指出在游牧帝国内多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发展,那种相信草原帝国的建立根源于其经济上不自足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狄宇宙
有关游牧人群和游牧政治体的问题总是一环扣一环: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究竟是自然的游牧单位的基本特性,还是游牧单位被组织进大型政治框架之后才具有的特性?游牧国家对农业定居文明所进行的周期性攻击,究竟是出于经济需求还是内部政治压力的某种释放?游牧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究竟何者才是最主要的动力?这一系列的问题,会促使我们在寻求匈奴帝国形成的历史原因时,从其外部转向内部,从经济因素转向政治因素。
匈奴帝国首先是一个政治构造。与古代一切大型政治体一样,匈奴国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人群与文化,绝不会是单一的语言、单一的族群和单一的文化。那种探求什么是匈奴语、什么是匈奴人的研究传统,就是把匈奴帝国的政治体属性与该帝国统治人群的社会体属性混淆起来了。建立了匈奴帝国的那个人群,也许与帝国内大多数人群在文化上本来非常不同,但历经漫长的政治与文化过程,统治集团在维持认同的同时,必定发生巨大的文化转型。
比如说,学术史上曾热烈讨论过匈奴说什么语言,绝大多数争论现在看来都已没有意义。这个问题的有效性应该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也就是问,后来建立了匈奴帝国的那个统治集团是说什么语言的?这涉及该集团原来在哪里,如何征服了草原上原有的社会(理应也存在一个或多个大型政治体)。有学者建议,匈奴是从漠南进入漠北的,他们在漠南时,是印欧语人群,进入漠北后逐渐被突厥化了。这个建议的史学背景是印欧语的东扩。如果我们接受“语言迁徙不意味着人群迁徙”的说法,印欧语东扩不一定是印欧语人群的东迁,而是印欧语所代表的某种文化(比如骑射和游牧)向东方发展。这种印欧语文化(甚至还有人群)的东扩,在陇山—黄河地带与春秋战国时代急剧崛起的华夏各政治体相遇,遭遇阻隔,其中的先锋集团如月氏和匈奴被迫向北发展,匈奴就是这样先入鄂尔多斯,后被日益强大的秦压迫到漠北的。
按照这个理解,匈奴在进入漠北之前,说某种印欧语(特别是某种Iranic)。但正如亦邻真先生所说,不管匈奴本来是说什么语言的,等他们在漠北安家落户以后,在那个突厥语(Turkic)的海洋里,他们最终都会突厥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匈奴帝国都是说某种或多种突厥语的,甚至也不全都是说阿尔泰语(Altaic)的。在匈奴帝国内,一定存在着众多的语言与文化,包括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多种语言、汉语和印欧语中的伊朗语(Iranic)各语言,甚至也不能排除芬—乌语系(Finno-Ugric)各语言。语言复杂丰富,意味着文化传统的复杂丰富。匈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复合体。把匈奴帝国范围内的某种单一的考古学特征视为“匈奴文化”,当作标准去检验其他考古发现,以确定是不是“匈奴”,这种做法首先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我们再回到蒙古戈壁。6世纪以后,突厥、回鹘、鞑靼乃至后来的蒙古,都以鄂尔浑河、塔米尔河的河谷地区作为其政治中心,甚至突厥之前的柔然也以这一地区为中心。那么,匈奴时期的政治中心是不是也在这里呢?从塔米尔河河谷的匈奴墓葬和三连城来看,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匈奴也曾经以这一地区作为战略后方。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全盛时期的匈奴帝国,其重心是在漠南还是在漠北?
把蒙古高原分隔为南北两个地理单元的蒙古戈壁,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称作“大漠”,清代的内蒙古和外蒙古,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就是由这片巨大的荒漠区分开来的。古代大漠以南的蒙古高原被称为漠南,以北的称为漠北。历史上的游牧帝国大多以漠北为中心,以漠南为前线,形成与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如果中原王朝军事上占有上风,游牧帝国会撤退到漠北,并俟机(一般是在秋冬之际)进入漠南实施袭击。中原王朝即使有足够的军事优势,通常也难以组织起对漠北的军事远征。历史上也只有汉朝对匈奴、北魏对柔然、明朝对北元、清朝对蒙古等有限的几次例外,其困难主要在于这片巨大的蒙古戈壁(大漠)。班固《燕然山铭》说:“遂陵高阙,下鸡麓,经碛卤,绝大漠。”所谓“绝大漠”,就是南北横跨大漠,从漠南进入漠北。这种跨越大漠的行为,古书上称作“绝漠”。宋代邵缉夸奖岳飞的词句说:“好是轻裘缓带,驱营阵,绝漠横行。”岳飞固然伟大,却实在并没有机会“绝漠横行”。真正实践过“绝漠横行”的中原将领是很少很少的。然而对于游牧军队来说,“绝漠横行”倒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燕然山铭》局部拓本
秦汉之际匈奴帝国崛起的时候,匈奴已经常常出现在长城以南,史书上说的单于庭大概在今内蒙古的中部,也就是在漠南。汉武帝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匈战争以后,匈奴单于庭迁至漠北,大概就在今鄂尔浑河流域。可是,匈奴是从漠南兴起的,还是兴起于漠北然后向漠南发展并吞并漠南诸游牧部落联盟,这依旧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西汉和东汉都曾经派遣远征军跨越大漠,在当时这意味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耗损,但是在能够承受这种耗损的汉朝统治者看来,只有这样的远征,才能真正对匈奴施以打击。
从读史的角度,“绝漠”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经历。2004年8月中旬,当结束对蒙古中部的考察之后,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小型的“绝漠”活动,当然不是像古人那样骑马、骑骆驼,而是乘坐俄制的“普罗冈”中巴越野车,从乌兰巴托出发,向南进入大漠直到中蒙边境。
乌兰巴托以南六十多公里的范围内基本上还是草原景象,可是快到乔伊尔时,满眼已是干旱区的戈壁景象。从乔伊尔向南,就算进入大漠了。地图上标志得很粗的公路,行车时却完全看不见,只有戈壁上的一点车辙。司机只好跟着车辙,傍着铁路和电线杆走。有时候颠簸十分厉害,而且还得常常停下车来找路。傍晚时分,到艾拉格(Ayrag),由此向南,渐渐进入大漠的中心地带。接近赛音山达的时候,地貌呈现严重的沙漠化景观。稀疏的枯草都看不到了,地面由粗砾石变为细沙。汽车进入柔软的路面后,速度明显降了下来。路边不断出现死去不久、尚未腐烂的骆驼、马和羊等,也可常见动物骷髅远远近近地散布在沙地上。动物尸骨保存得这样好,证明这里连食腐动物都很少,生态之恶劣可见一斑。
赛音山达是东戈壁省的省会。蒙语赛音山达的意思是“好水池”,可它偏偏又是蒙古国最干燥多尘的省会之一。第二天清晨,我们曾在安静的赛音山达闲走,看这个还在享受晨梦的城市。城北高岗上,有一座坦克纪念碑。爬到纪念碑旁,向南俯视赛音山达,只见沙漠包裹之中的这座戈壁小城,如同黄色波涛里的一叶孤舟。
从赛音山达到中蒙边境,我们同样是在沙漠与戈壁相间的地貌中颠簸前行,慢慢地,地面有了青色,黄沙渐少,浅草渐多,虽然与草原还有很大差别,但毕竟不是那种荒漠景观了。偶尔能看到牧人和畜群,看到几峰骆驼傲慢地立在浅草戈壁中。这说明我们已经来到大漠的边缘,离中国边境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们所选择的绝漠“捷径”,靠性能优越的汽车尚且费时两天,在古代靠骑马、骑骆驼,必定需要十天左右。大漠内少有水泉,人畜饮水必须随身携带,大规模行军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对于游牧人来说,在艰苦环境中求生存是与生俱来的本领,大漠不是他们自己南北穿行的“天堑”,而是他们防卫南方定居社会远征军的天然屏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绝漠体验,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匈奴帝国内部的政治地理构造,但绝对有助于我理解匈奴何以能够与空前强盛的汉朝长期对抗。
2004年和2006年的两个夏天里,在蒙古高原的图拉河和鄂尔浑河巨大的河谷草原上,在森林密布的杭爱山,在巍峨高峻的阿尔泰山,在黄沙漫漫的大漠深处,我们寻觅着匈奴的踪迹,尝试着解析有关匈奴历史的种种神秘。有趣的是,当旧的疑问还没有答案时,新的问题已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疑惑,牵引我们越来越深入遥远而又切近的匈奴世界。我们相信,在蒙古戈壁(大漠)以北,不仅仅在蒙古高原,而且在辽阔壮丽的外贝加尔和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有关匈奴历史种种疑问的答案。来年夏日的晨风吹起时,我们还会整顿行装,继续靠近那些敛迹于蓝天绿草之间的答案。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东方历史评论》,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